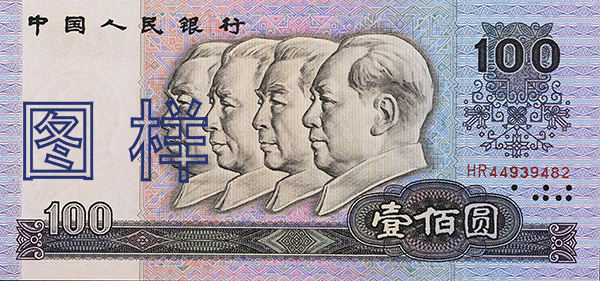俯瞰佛坪县城。

县城跳广场舞的人。

佛坪县城区图。

政府楼里各部门的信箱。

夜晚的老街。
在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有的以蔬菜集散中心闻名,有的将小吃开遍全国,有的县是快递业巨头,有的县盛产网络主播,有的县每年生产7亿双运动鞋,而佛坪县以人少著称。
佛坪县是陕西人口最少的县,常住人口3.02万人,不到郑州大学人数的一半,一栋互联网总部大楼就能装下全县人。安徽临泉县人口超过200万,是佛坪县的67倍。从GDP来看,全国百强县之首昆山是佛坪的352倍。
这里生活着大熊猫和金丝猴,有时候,动物的新闻比人的多。这里熟人多,很多人是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不少情侣走在街上,不可避免地遇到前任。
县城无论大小贫富,都有一套行政建制支持运转。一家几口都是公务员的现象并不少见。
没有红绿灯和网约车,也没有肯德基和外卖
从西安坐高铁向南,穿过层层叠叠的秦岭隧道,抵达一块被大山包围着像鞋底的狭长平地,就是佛坪县城了。
这里没有红绿灯,没有网约车,出租车有9辆。
出租车司机翟小涛子承父业,从父亲手中接过方向盘,“佛坪很多人都有我的电话”。县城十几分钟就跑完了,他主要往农村跑,谁家小孩拉肚子、发烧、孕妇不方便了,都给他打电话,山里的沟沟堑堑几乎快跑遍了。虽然车辆不多,但交通局和运管所的配置齐全。
桥头的十字路口几乎是县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一到傍晚,就进入广场舞时间。退了休的男人“上班式”地在路边打牌下棋,与上下班的人保持着一致的节奏。
一年两次,县城可以用“人头攒动”来形容,一是临近年关,购买年货的人填满了县委县政府前的街道。当地农民的菜摊摆在路边,讨价还价的嘈杂声、刀剁在肉案上的砰砰声,声色交融。在县城几乎走几分钟就能遇到熟人亲切招呼。
另一次是夏天的“秦岭大熊猫文化旅游节”,拍照的游客挤在街上,网红也来直播“带你游佛坪”。
余下的大部分时间,人都是不多的。一个名叫“烤鸭店”的烤鸭店挂着自转的烤鸭,瞧不见店主人。一处名叫“鲜花阁”的花店在上午11点仍然关着门。
佛坪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唯一一家类似的店铺叫“乐麦客”,招牌下写着“中西式复合餐厅”。县城没有咖啡馆,奶茶店也很难觅得踪影。县城的文旅大厦里有一家电影院,一共两个影厅。
曾经有个90后试图在家乡搞外卖生意,但很快倒闭了。同样倒闭的,还有一家健身房,占地一层楼,墙上的运动标语已经褪色。
虽然商贸称不上发达,县里还是完备地配置了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食品药品稽查大队、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中心、中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节能监察中心、以工代赈办公室、价格认定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办公室、手工业管理办公室以及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一家有7个包间的餐厅的老板说,在佛坪“干中餐的不如卖面的,卖面的不如卖馍的”。生意越小,生意越好。卖炕炕馍(当地特色小吃)的一天能卖出两三百个,老板的脸被做成表情包,在县城人的微信群里流传,几乎人人认识。
经济发展靠什么
在县城常能看见拎着尼龙公文包的年轻人疾步行走。一公里的街上有交通局、妇幼保健站、消防大队、公安局、交警大队、文化中心、电信局、教育体育局、环保局、地税局、林业局、农业局和水利局。
在另一条更短的街,会依次路过扶贫办、民政局、财政局、检察院、工商局、住建局、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折返时经过气象局、法院、电力局和劳动服务局。一位老县城人到了60岁才知道深山里的家乡还有一个海事局。
佛坪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介绍,截至2020年年底,全县有各类编制2194名,其中行政编制640名,事业编制1554名。根据《佛坪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2991人。一份2005年的佛坪县财政支出统计表显示,当年行政管理费支出1802万元,排在支出的首位,占全年总支出的37%。那一年的经济建设支出是405万元。
在佛坪,工商业发展相对缓慢。
山茱萸是佛坪的特产,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细小黄花吸引着外地游客,等到秋天,结成红红的果实,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成分。山茱萸虽是难得的资源,但这些年来从技术、融资,到产业链的延伸上都发展困难。当地人在冬天看到个儿大肉厚的山茱萸烂在树上,内心惋惜,“卖的钱连摘它的工钱都覆盖不了”。
除了做药材,当地想把山茱萸做成食品,却很难在技术上突破,产品要么酸涩,要么失去营养价值。
1999年和2000年,工商银行佛坪县支行和建设银行佛坪县支行相继撤销。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建议优化县级行政区划,她说,越是人口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县人口流失越严重。西部某省52%的县人口流失。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她因此建议,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小县进行合并试点,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关于合并的说法,一直刺激着关注佛坪命运的人的神经。当被问到合并的传言时,一些公务员摇着头不想讨论。
1958年,佛坪县制撤销,境内辖地岭北划归周至县,岭南分别划入洋县和石泉县。“鉴于大县大社不利于管理,1961年又恢复佛坪县建制。”
一些不愿合并的人认为,佛坪处在两县之间,距离两边都较远,合并后将不利于管理。而且此地有大熊猫,又是引汉济渭工程的涵养地,功能特殊。县的设置除考虑人口和版图因素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管理、军事等多个维度。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杜金锋认为,撤县要考虑县城原先辐射范围的人口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撤县后相应的设施等级会降低,如农村人口看病会更不方便。
他曾跟澳大利亚的学者交流,那里地广人稀的地区,没有配置医院,但会派直升机定点为居民检查。这提供了一种思路,“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在区域间流动,而不是静止的。”
杜金锋说,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产业,“公务员经济县”中,公务员对当地的经济只能是保障,而不是促进。撤县后,当地的消费将继续萎缩。
“未来撤不撤县,核心是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合并后,还能否保证剩下人的生活便利。”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悦中山表示。
佛坪有两处公园建在山上,山里人把登山当做一件苦事,而不是娱乐,因此有人一年也没去过一次公园。“这里的需求不是公园,本身就在自然景观里,也许健身设施才更有吸引力。”杜金锋提到,无论从机构设置还是公共服务设施来说,县城参照了大城市的标准,实际上应该因地制宜,满足当地人的需求。
离开的
人少是先天不足加人口流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前,佛坪县城仅有南北走向一条300米的街道,城内居民不足1000人,现在县城内的常住人口有8000人左右。
1990年,全县人口35710人;2010年,变成32999人;2019年,全县常住人口30181人,30年间,总人口减少5529人。
记者遇见陈丽颖时,她是县城图书馆里唯一的读者。图书馆相对迷你,一楼只有两面墙的书架,种植技术书籍与世界名著并列。陈丽颖出生于1993年,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一本厚书。
“我不属于这里,总有一天会走的。”她在江苏的一所学校学习艺术,后来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她得到一个在西安的大专当教师的机会。
“当时我父母不让我去西安,一定让我留在这里工作,那个机会就错过了。”陈丽颖花了半年时间消化这件事,现在提起来仍心有不甘,“讲的科目也是我喜欢的,艺术史。”她回家后,在少年宫做美术教师,教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画画。
她想给县城带来不一样的东西,给学生看设计感很强的建筑,比如线条流畅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孩子们却显得躁动,不能接受这些“怪建筑”。
有一个学期,陈丽颖尝试大城市的教学方法,给孩子们一个主题,让他们自由发挥作画。结果发现,很多学生什么都画不出。后来,她恢复了传统的教学,自己画一个,底下的学生跟着她画。
“你怪小孩没有想象力吗,想象的前提是基于生活,很多东西他们没有接触过,怎么去创造?”
县城在重山阻隔中,多年保持着弱小的格局。她已决定在今年夏天离开。那本厚厚的书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她还是想找回当初那个机会,去高校工作。
一位从佛坪到北京打工的90后始终记得离家的场景。那是2008年,外出还没有高铁,父母送他到汽车站,走了30分钟。他们提着他的包,给他买了新衣服,担忧着儿子的第一次远行。儿子望着父母的背影,像很多远离家乡的人一样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改变这个家庭。
黄文庆1978年坐林场拉运木料的解放牌汽车来到佛坪,3年后进入佛坪中学任教,直到上完高三最后一课退休,大半生几乎都在佛坪,是这里唯一的特级教师。
“高中难办,大量学生到平川上学。”县城里条件还行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汉中或是西安的寄宿学校读书,一到周五,有“大部队”的家长奔赴城市给孩子送吃的、洗衣服。同一时间,汉中一所私立学校会派两辆大巴车把学生送到佛坪汽车站。
县里只有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一共1089个学生。唯一稍显拥挤并在建设第二所的学校是幼儿园。
从佛坪中学考出去的师范生基本都没回来。一个高三学生在店里打工,她正准备读一所高职,她说这些年学校一年没有几个人考上一本,考上名牌大学的几乎没有。她的同学八成来自农村,在绿水青山里长大的她觉得西安“是很美的地方”。她有些害羞,没出过远门,只在短视频里搜索听过的地名,一个一个划着看。
佛坪中学的教师最费心力的是招生。每年中考的前30名,能留下10个在本地读书已算不错,即便学费住宿费全免,外加奖学金,还是难以让学生留下,教师的孩子也会出去读书。
“人少的地方往往偏僻,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现代文明也不容易进来。”黄文庆说。
佛坪只有一家被代管的医院,两辆救护车长期安静地停在门口。
许多县城人生孩子都选择到山外的都市,虽然佛坪配置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大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老龄健康服务中心。
不大的新华书店,里面多一半是儿童的书,店员说“现在大人看书太少了,基本不看”。书店前是固定牌摊,招牌下有一半店面售卖鸡爪。记者去时,博物馆里,展示民俗的假人比游客多。
黄文庆记得,许多年前,县文化馆订了一本杂志叫《兵器》。很多人议论,“订这本杂志有啥用,你制造兵器吗?”“人们的观念是实用的,殊不知这是人的求知欲。”黄文庆说。
他主编了当地的期刊《佛坪文艺》,出版了17期,“演员少,舞台上转来转去就是那些人亮相。”即便这群最活跃的文化人,也从未在佛坪搞过一次文化沙龙。
不久前,这里刚成立了一个体制内的单位:文联。
黄文庆说,小县城人长期以来有意识的惯性,对大城市无比向往。
杜金锋曾做过异地扶贫搬迁的调研,当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流动是一种必然。他调研的一户人家,必须要挑水喝,单趟就30分钟,一个40岁的壮劳力没有外出打工的唯一理由是给父母挑水。
无论是从农村到县城,还是从县城到大城市,悦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的县城总体人口规模在缩小,人口外流是趋势。他在汉中调研,当地去年有340万人,今年只有320万,政府也在担忧人口的流失。西安户籍放开后,渭南市一年流失近14万人。杜金锋在陕南的调查显示,农村在过去几年减少了30%人口,商洛市减少了38% 。
但悦中山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只要放开限制,未来自然会有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人们用脚投票。”
留下的
县城桥头最明显的位置挂着一张巨幅广告,“××教育”——一家培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的机构。扫广告上的二维码,“××帮你盯公告,第一时间获取职位表,不必熬夜,不会错过!”还会送上事业单位考试冲刺密卷。
很多留下的年轻人没有过多选择,希望跳入有编制的池子中。
有人考到超龄仍没考上,有人为考编制已经花了十几万元,并仍在继续。有的考生提个箱子,随时出发,哪里有考试奔哪里,远至苏州。有的跟大学里的老师打好招呼,逃掉课程,一门心思备考。
县城工作的优先级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相亲时,女孩只要有编,家底不错,再打扮一下,就是“白富美”了。
硕士毕业的陈丽颖在当地算是高材生,别人问她在哪个单位工作,她答自己没有编制、不在系统里,“对方的微表情很让人难受”。
县城的建筑中,有两栋商品房高楼建于10年前,剩下大多是家属楼和自建房,以林业局的高楼为最,林业局在这片山林里是抢手部门,热门的还有“管人的和管钱的”部门。
2019年,佛坪招了20多个行政编和50多个事业编,“有编制才能把人才留住。”编办工作人员说。为了腾位子,有的干部51岁退二线。
一位在基层的选调生说,工作是扶贫、各种填表、处理纠纷,一个几百人的村子,一年能用掉几十箱A4纸。
在政府部门工作,有些人中午溜达着回家吃饭睡个午觉。一位养猪户说这里是山区,养猪的人少,管理畜牧业的部门可能清闲。
也有公务员感受到的是繁忙,最近一年,某公务员没在零点前睡过觉,一次到了下午3点,她感到心慌,才意识到还没吃午饭。
退休教师黄文庆愿意女儿女婿在体制内工作,“平平稳稳,生存有保障”。他年轻时教学出了名,市里的私立学校来挖人,工资翻一番,提供一套房,他拒绝了,“我还是觉得体制内更保险。”
“受传统意识影响,吃官家饭,也是种荣耀。”黄文庆说,“在佛坪,创业的很少。”
姜东属于“异类”,他是佛坪电商第一人,1987年出生,长期在外打工,2014年回乡创业。
“结婚后,总要落叶归根”。他看到家乡山里的棕榈能做成床垫,便和妻子创立了公司,早期不懂电商,印了广告单到江苏、山东一带跑市场,收效甚微。一次在火车上遇到妻子的一位东北老乡,才开始有了第一张、第10张、第100张床垫的销路。因为处在山里,每天的运费都要贵50元。“我们在外面见识过别人的事业心,人总是不甘于平凡。”
创业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里,父母一看到货码在那,赚不到钱,矛盾就来了。严重的时候,他跟父亲几个月不说话。直到家人听到手机“叮咚”一响,订单来了,气氛才缓和。
另一重阻挠是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外地买家找不到厂子,在村里问路,有村民就说他家床垫如何不好。“嫉妒你说明自己本身胆小,他敢去银行贷款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创业吗?”
观念的束缚之外,创业也面临着缺人的问题。姜东想聘请一些优秀的电商人才,发现“少得很,要么就是半吊子”。
村民大多没有在工厂工作的经验,不了解规章制度。很多人在工地做习惯了,累了就在地上一坐。住在周边的人,家里有事总要请假,来回几个小时,如何计算工资。
一位50岁的工人分配到的任务是晾晒棕,姜东发现他的心思不在活儿上,而是偷瞄着老板,如果老板不在,他宁可在太阳下暴晒,也不三下两下把活儿弄完去阴凉下歇着。
“他们听我谈产品听不懂。我说这个东西敢不敢搞一下,他们说,‘什么东西,骗人的吧?’”
他所在的村子叫银厂沟,端一碗饭,没吃完就能走遍村子。村里只有375人,去年死亡3人,出生2人。姜东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喜欢走亲访友。他感到这些年,村庄少有孩子嬉笑打闹的声音,也少有猪叫和狗叫,有的人家大门一锁,几天看不到人。以前大家聊天的大碾盘,现在建成了停车场。他有时怀念小时候一群孩子拿着镰刀去打猪草,旁边跟着小花狗的日子。
姜东在银厂沟常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好像你跟不打游戏的人解释这个道具如何好,别人听不懂”。在南方,他遇到问题,找个茶社,叫几个朋友出来聊,总是能找到问题的核心,“就像文艺复兴时候,那么多思想一起碰撞”。在这里,人们习惯反问他“有啥用”。
城市综合征
一位当地人曾外出打工,坐42个小时火车,落地广州。一出站,就混入人群中。她在东莞的车间里加工工艺品,“天使的翅膀”和会发光的摆件,一年后回家, 孩子叫她阿姨,不叫妈妈。 “孩子不认我了,还打什么工”。
2017年佛坪开通了高铁,成为县里的大事。这是当地领导努力争取的结果,被浓墨重彩地写进县志里。自1825年设立佛坪厅,县城建制几经变迁,尽管人少,佛坪在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县的地位。
为了能有人气,佛坪想了许多法子,比如紧紧攥住大熊猫这张名片。山上的广告牌、高铁站的拱门、桥头的装饰、姜东的棕榈床垫上,全是熊猫的身影。
佛坪的人类活动较少,秦岭又为熊猫提供了十多种竹类,使得这里成为国宝的栖息地。当地曾推算,佛坪境内每100平方公里有大熊猫7.8只,密度为全国最高。
在《佛坪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人们能看到佛坪的发展。
初步核算,201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14767万元,比上年增长8.1%。农林牧渔业完成总产值33463万元,比上年增长4.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6618万元,同比增长13.2%。全年接待游客197.6万人次。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公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6.03%。
公报还提到,佛坪主动出击招引项目,建立招商引资联席会议制度开辟重大招商项目、重点工程项目“绿色通道”,举办首届“古道明珠、静美佛坪”招商推介活动。
黄文庆说,过去讲究“人定胜天”“人海战术”,人少的地方都有种自卑。现在科技发展了,许多事情不靠人数决定。“佛坪人口虽少,但人均绿地、蓝天、氧气的比例很高”。
他热爱这个工作了半辈子的地方。2002年,佛坪遭遇洪水,237人死亡或失踪。救援队带着物资和药品乘直升机来灾区探望,螺旋桨卷起地上的灰尘,黄文庆看到,许多佛坪人哭了。
这里地广人稀,人们往往比都市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小学同学很可能还是初中同学,也是高中同学。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机关单位,面熟的人多。下班后朋友打来电话,相约一起烧烤,人们骑着电瓶车就去了。烧烤店老板也是认识多年的,大家对每道菜都熟悉。
熟人太多有时带来一些麻烦,人们吃饭喜欢去包间,在大堂,熟人多,少不了要多敬几杯酒。还有人吃早点时背对着大门,不然一个馍还没吃完,就抬头跟人打了十几次招呼。
黄文庆喜欢这里的人情味儿。过去走在街上,谁家女子、谁家老汉都清清楚楚,哪一户来了客,几乎整个县城都知道。
即便不知道对方名字,也很可能了解他家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兄弟姐妹几个。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一方有隐疾,另一方不知道,马上有人从好几代前说起。
相亲在这里很普遍,一位当地年轻人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西安商场打工的女士,两人匆匆见了一面。他最终娶到她的方式是讨好她在当地的家人,秋收的季节去地里摘玉米、过节了带着礼品探望、修房子跑去帮忙,这期间他没再见过女方,直到她回家,相处了几个月,他便提着四色礼(烟酒等)上门提议把婚事定下。
中等家庭结婚时起码有四五十桌酒席,有的有八九十桌。这里的人很大一部分支出是人情份子,有人估算,一个公务员一年的份子钱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收入。
在这样的人情社会里,言论、道德、口碑就能约束一个人,悦中山说,一般不用动用法律。这里的犯罪率很低,一是犯了事在山里跑不出去,二是人和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讲究人情的地方也容易忽视制度,若在圈子里,很容易得到资源,如果不在就被排斥,“影响了整体的公平。”悦中山说。
留在这里的人则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节奏,上了年纪的人安静地坐在老街两侧,与面前的一排盆栽一同晒太阳。过去几百年,佛坪人一直在这块勉强平整的土地上平静生存。入夜,圆月照着青山轮廓,像古诗画面。
一位老县城人说自己患有城市综合征,一到大城市,呼吸也急促了,听力也不行了,心慌得很。一进山,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他退休后,爱好养花、去河里捡奇石、集邮,还种了一小块地。
“也许未来佛坪会成为秦岭里的后花园。”悦中山说。
(文中陈丽颖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原标题:这个县只有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