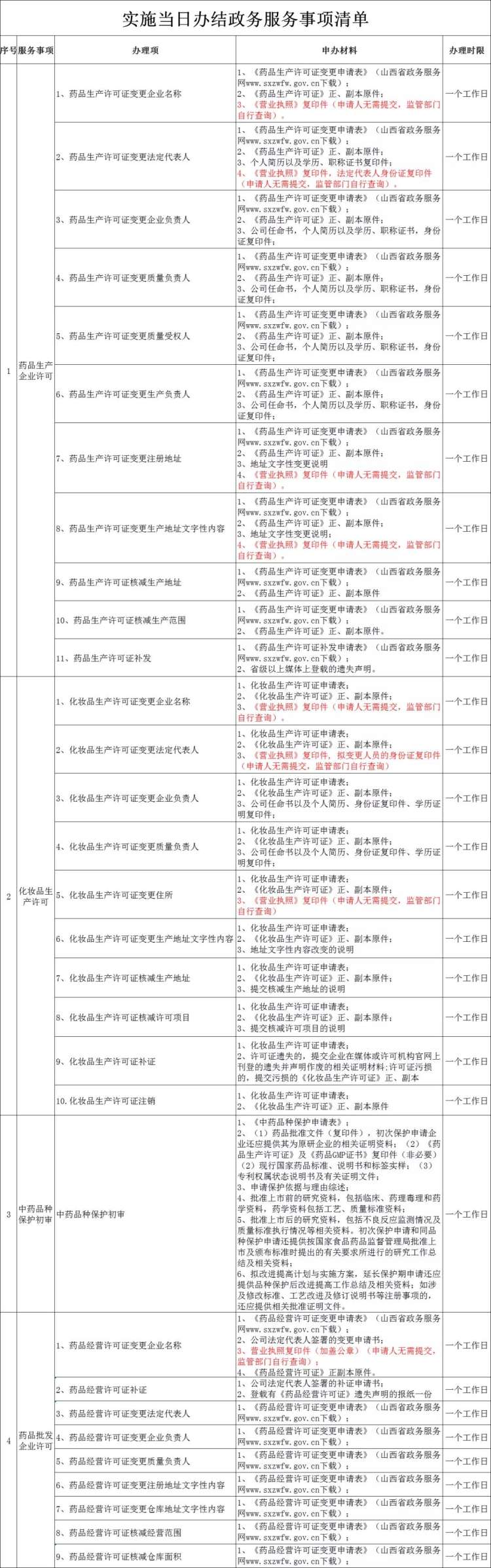说起雁门关,人们通常会想到唐朝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诗人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战争画卷,原来车毂交错,横刀立马的大场面通过汉文字的诠释,还可以这样排列——黑云压城,甲光向日,角声满天,霜重鼓寒……也许正是源于唐诗的力量吧,现实的雁门关与我心中的构想不谋而合。前腰铺驿站、阜戈寨民居、十八弯关道,还有雁门关关城的主体建筑,仿佛是从线装的古书里一样一样移出来,复归原位。尽管有一些摹造和复古的意味,但清幽静谧,古拙苍凉的格调还是把我带到一个遥远而时局动荡的年代。循那样曲折的关道,攀那样宏丽的城墙,感知那样山环水合的形势,总觉得这里刚刚平息一场鏖战,利镞穿骨,旗靡辙乱,一匹失去主人的战马嘶啸着没入山谷……从未见过如此高远的天空,从未见过如此雄浑的关城,哪怕是两根悬着方形刁斗的石幡杆,都有着参天气象。还有呢?还有就是镇边寺外两只石狮子,雁楼之上的“中华第一关”的牌匾……对游人而言,雁门关随便的一匾一联、一堞一楼都可以切身感受到千载之前戍边将士剧烈呼吸的撞击,即使是天险门、地利门上的石刻题额,也摸不透铁马秋风的剽悍。这样的地方本身就是供人怀古的,壮怀激烈的情愫可以贯穿每一个游客的胸襟。明洪武七年的春天,声名显赫的吉安侯陆仲亨因触犯了朱元璋的官制,被罚往代县拘捕盗贼。作为开国功臣的吉安侯并未因贬谪而意志消沉,在他整饬代县军务期间,面对退居漠北的北元势力常怀惕惕,尤其在巡视日渐残缺的古雁门关后,做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移筑雁门关。于是,600多年前的雁门山谷,沸扬起一片有节奏的斧凿之声。新的关城落成后,吉安侯陆仲亨卓立在高耸入云的雁塔旁,谛听北方隐约传来的羯鼓胡音和大漠边声,不禁长吁一口气。在冷兵器时代,天险地利的优势往往是决定战争走向不可或缺的条件,行伍出身的陆仲亨深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道理,经他监修的关城如同一把铁锁,锁死了通往中原腹地的大门,纵使瓦剌或鞑靼人疯狂的马蹄也只能在广武城以北的莽原地带逡巡了。对古老的代州而言,雁门关既是当地百姓赖以安居乐业的庇护神,同时又把他们推到了战争的风口浪尖。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古人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沿着长城走向,历数那些雄关险隘,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玉门关……发生在每一道关隘前的战争,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烈度和密度上看,都与雁门关相去甚远。北方鞍马部族不断南犯的捷径不在西北、不在东北,而在我的脚下,中原几千年的物质与文化的富庶成为引弓之国垂涎三尺的缘起。所以,依山就势,设立关隘,没有什么不妥。从风起云涌的战国起,一直到火药广泛应用的明朝,雁门关的军事位置日显突出,已上升到兵家必争的高度。雁门山山形下陷形成的沟谷,为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部落提供了进入中原的门户。关城的设置,一定程度上阻遏和延缓了这种入侵的进程。600多年时光让我们陌生了这座关城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例,同时也陌生了那个身着飞鱼服重修雁门关的吉安侯。但天险门我还认得,地利门我也认得,还有瓮城围城,还有镇边寺、壮士亭、明月楼,还有通往关楼的每一级台阶、每一眼砖券的门洞和深雕汉辙唐辕的古关道……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甚至人们口口相传的李牧、李广、薛仁贵、杨家将的故事,我们都曾听过,并且耳熟能详。600多年前的明朝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了,1000多年前的唐朝呢?1000多年前唐朝戍士手执刀枪剑戟斧钺勾叉,沿另一条更加曲折的关道,走向白云缭绕的西陉关。西陉关是雁门关另一个名字。那时的关城,山岩峭拔,雉堞崔嵬,运送粮秣的马车夹杂在驰援士卒的队伍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西陉关外呢?西陉关外则是另一番景象,风卷着风,沙扬着沙,兵如潮涌,矢若飞蝗……直至今天,人们仍可以从西陉关的废墟里翻捡到唐宋时期遗落的残戟断锷。那时,雁门关被一匹烈马拖曳着,洒一路热血,慢慢渗入胭脂色的石罅里,冷却成冰。英雄的雁门关经历了太多太多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以至于时隔千载,当我登临修葺后的雁门关城楼,仍觉得脚下的城墙在缥缈的金戈杀伐声中不断战栗。鸟瞰那一条曲曲弯弯的关道,目光从容地伸向历史纵深;猜想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关道,仿佛先民在故意延宕接触战争的距离。关道的一头是当下安逸鲜活的时光;另一头联袂着尘封了几百年,甚或上千年的一份染血的战表。一些披坚执锐的将士,缓缓顺着关城的台阶走上来,他们说说笑笑,表情恬淡而闲适,谈论着战争以外的话题——灞桥折柳,岭南来书。雁门关的故事里不单只有喋血沙场的悲壮。终于有一天,乱云飞渡的雁门关沉寂下来,我们看到战败的单于走远了,马背上的耶律氏落寞在如血的残阳里,失意的可汗也渐渐消弭在阴山下的敕勒川……这是历史的必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古老的雁门关被风尘和历史剥蚀得只剩下年轮,雁门关俨然一个折戟沉沙的勇士。风寒里形容枯槁的雁楼,坍圮成一堆废墟的李牧祠,以及荒草萋萋的古关道,都在为那个“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的累累盛名而颇感愧疚。一代雄关,荒凉若此,非一般的隐忍所能承担。而今,经过大修后的雁门关,已再现昔日的雄姿。汉白玉的雁靖坊高标挺然;横贯于关南关北的青石关道焕发着苍古的韵味;在阜戈寨民俗村的泥墙下面,依然蛰伏着先民寻常生活的五味杂陈;前腰铺驿站进进出出的游人,似乎都是些持有勘合或火牌的邮差,他们十万火急地由京师而来或从雁门而去,怀揣的不是边关告急的文书,就是兵动塞外的带钩虎符;倒是云际泉里的游鱼悠然置身物外,清涟的泉水却有更加久远的沧桑倒映在上面……假使当年的吉安侯,突然身着绣有流云飞鱼海浪江崖图案的飞鱼服,英姿飒爽地回来了,他也一定会被雁门关的恢宏气势所惊讶和叹服。雁门关风光如旧。其实呢,只要看过雁门关南那座代县城的文庙和边靖楼,就可以想象几个世纪之前的代州一带的城镇与乡村是怎样的鼎盛和繁华了,这样的繁华建立在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基础之上,同时与蜿蜒于雁门山、馒头山、草垛山上的古长城和那座巍然耸立的雁门关有着莫大关联,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雁门关的存在,代州、山西,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史,将被草原强大的军事风暴扫荡得面目皆非。铁马秋风,雄关漫道,雁门关应该是汉民族的一幅气势雄峻的中堂。这幅中堂构图旷远,敷色简淡,画中的人物因时间的流动不断变换和叠加着,所渲染的故事情节却大体仿佛。一幅中堂往往有契合画风的题诗,雁门关的题诗是李贺的名篇《雁门太守行》,挥毫着墨的偏偏不是李贺本人,而是一群髭髯猬张的武夫,是一群甲胄鲜亮、马策刀环的将军或士兵。这样,行文就有些潦草,沾了霸气和草莽之气,笔锋反显得苍劲有力、沉顿雄奇了。
杨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