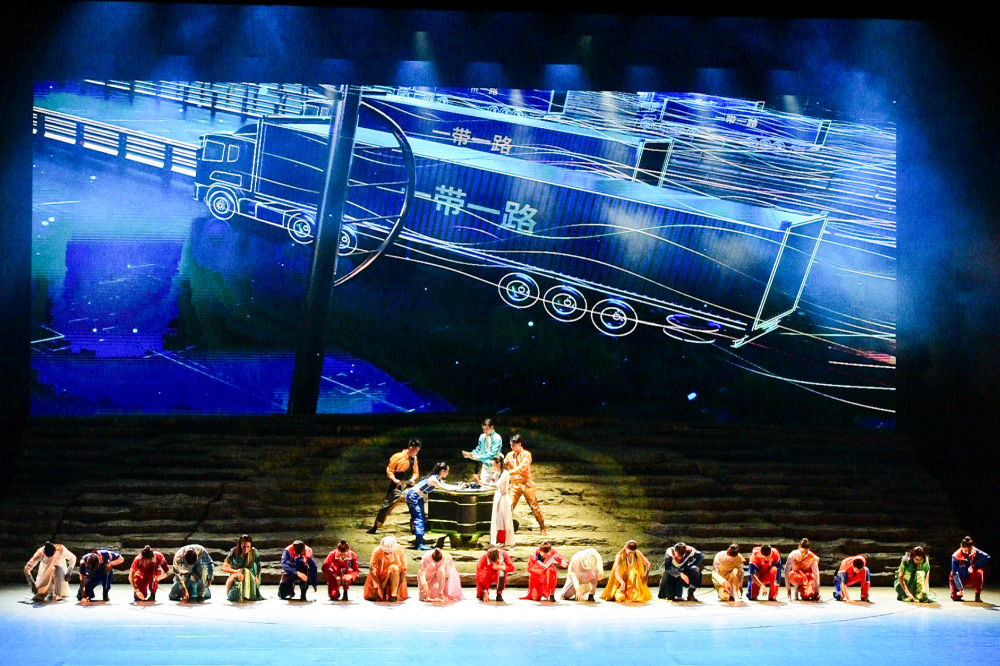1 5月间我来到乡间,我钻进房屋与山壁之间的一条缝隙里,我看到几枚钱币那样小的阳光,一只箩筐,几颗石子,土色在狭窄间发出暗的光……我像乘上魔法车,瞬间就抵达了童年,我那遥远的故乡。当我从里面钻出来,槐花开放,梨树安宁,香椿树叶在房顶上面飘扬,一只猫却睡在黑凉的煤堆上。废弃的小学校,那三间苍凉的土房,开始吟唱旧年的歌,门口那块宽大的沙石邀请我的屁股,于是我便落座。一旦坐进这童年之家,那滚滚而来的心绪里,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悲伤。但我那存放在时光里的喜悦,这时候,就像地平线上的一匹红马,奔腾而来。那上面坐着过去的我,我勒紧缰绳,夹住马肚子,催促它,惟恐它越不过时间的山坡。当然,最后我们很快相遇了。这时候我走到并站立在一棵山楂树前。2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以前的想法是,当不当一个作家是无所谓的,我只想做一个人。现在,今天,此刻,我想当一个作家,我感到一股巨大的从未有过的渴望,像海浪一样冲击着我。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我的灵魂因此而受损,哪怕我的身体亏空,哪怕我不断地丧失,直到一无所有,哪怕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得见乞丐眼中的垃圾,哪怕我变成一个聋子,只听得见永恒的虚无之声从我的耳旁呼呼刮过,而我像一株冬天的树,所有的叶子都已脱落,像内蒙古高原上的树,被全面地剥夺,显得孤高而病弱,我只盼望那惟一的享乐,那就是,眼望着时间之河,以及漂流其上的垃圾,那些无人想望的东西,哪怕我来不及或者没有能力把它打捞起来,我只要看得见……3我与围棋的关系正在变得疏远。在将近20年里,我终日与它为伴,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我的工作时间。我没有为此惭愧。我做任何事或不做任何事都不曾后悔过。人生是一场游戏,围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人生的浓缩。在所有棋类中,甚至在所有游戏中,它是最当得起这一称颂的。围棋给了我很多很多。让我写几行文字,来纪念这我和它的已经可以看得见的结局吧。围棋把世俗生活的智慧简化在棋盘上,使得从勾栏瓦肆到宫庭争斗的世俗的勾当也成为了一种美;它让时间的流水快速地从我身边流过,减轻了时间对我的重压;它黑白两色的古雅的艺术构造,使我认识到艺术的精炼原则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它在艺术之美与追求效能的结合上,给了我重大的启发,让我在写作上始终坚持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能让它成为一颗“废子”,因为一个浪费了的词和棋盘上的一颗“废子”一样,成为了一种无用之丑的见证,它能令人的智慧羞惭;围棋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语言,一是刀光剑影的所谓手谈,二是人们从千百年的手谈中总结出的那么多的围棋术语。在手谈中,两个人的对话可以接通千古风云;在围棋的一系列术语里,我体会到,一个概念可以和生活结合得多么紧密,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用的概念,它们只稍稍高出棋盘之上,它们笼罩着棋盘,就像台灯的柔光笼罩夜晚的写字台一样,既光亮又温暖;但是,随着围棋的日益商业化,对于胜负的敏感减弱了它的其他的美,它沦为了残酷的竞技,而永不再是智者的交谈,它成了外部和内部规则的双重束缚之物。这也是我与它终于疏远的原因之一。我将离开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适合丛林法则下的生存,而围棋的商业化正是丛林法则的上演。4写信是交谈的较高级形式。在电脑网络发明和普及之前,书信是必要和珍贵的。现在,电子信件普遍地被人轻视。人们在写它时,内在的庄严感一点也没了。物体的运行速度改变了物体的本质。但在人们厌弃书信的时候,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书信的本质没有完全改变,它的珍贵,它对于存在的独特的勘探方式,仍然是有用的。第一,书信是情感和思想最为紧密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可能除了某种类型的日记,没有任何文体能出其右;第二,书信是两个人的谈话,它具有优雅的隐秘性,它完全有别于网络时代众声喧哗中的公开的独语;第三,书信仍然是对特定收信人的寻找,它带着写信人内在的特征和热情,去寻找一个同路人,它是孤独在我们时代散发出温暖的极少数形式之一。而网络时代别的方式几乎都成了呆头呆脑的待售,成了客户面对全体主顾不顾尊严的摇尾乞怜;第四,书信是勇敢的,无论电子信件如何快速,毕竟仍然发生了一个人在路上的过程,这还不说它可能会被拒绝,当成垃圾被扔掉的可能性。因此,它所进行的是一场下临深渊的单独的飞翔。书信的上述本质在网络时代并没有被改变,而是人们认为它改变了。5我们时常有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这种时候,只要站得起来,甚至仅仅是坐得起来,我们就应该继续工作。精神上不适的时候,也应该如此。因为,工作是治愈所有疾病的良药。而且,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最大限度地投入工作,身体内缺少了氧气,我们的身体才有了病。很多病只是对于懒惰的抗议。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身体或精神所感到的不适,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我们应该通过工作的渠道,让那些软弱流露出来,因为当我们重新强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每一次的软弱都是不同的,都有它的特征,色彩,气味和强度,在最软弱的时候,上述各种的表现反而最为强烈。应该拍摄下这人心中低凹地带的景色,应给予它与高处的风光完全平等的位置和价值。显然,这项工作只能由病人自己来完成。那么,康复之后的回忆能不能达到同样的真实记录的目的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强健者已经重新恢复了他的傲慢,他已经忘记了悲伤。6太聪明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凡事总有例外,比如纳博科夫就是太聪明的好作家,海明威也是,但这样的好作家太少太少了。托尔斯泰的叙述像一整座山在移动,妥斯陀也夫斯基如火山喷发,卡夫卡像一只老鼠在看不见的阴暗里挖掘。他们都带有了自然界的某种属性,他们的技艺因此成为看不见的,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固执、偏见和不通人性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增添了人类的经验,更新了人性的概念。而且,即使是纳博科夫和海明威,也稍稍低于上述作家。这正是好与伟大,优美与崇高的差别。太聪明的作家就不会太固执,他们一定要跟别人在技艺上比高下,他们忽视了艺术应以高于艺术的东西为范本;而且他们太人性了,他们隐藏或掩盖了自然留在他们身上的瑕疵,这是他们运用他们的聪明过度锤炼艺术炼金术的后果。但是,太聪明,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属性。因为智慧是无法超越它本身的,太聪明的作家只能在一种优越的宿命里生存。
□聂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