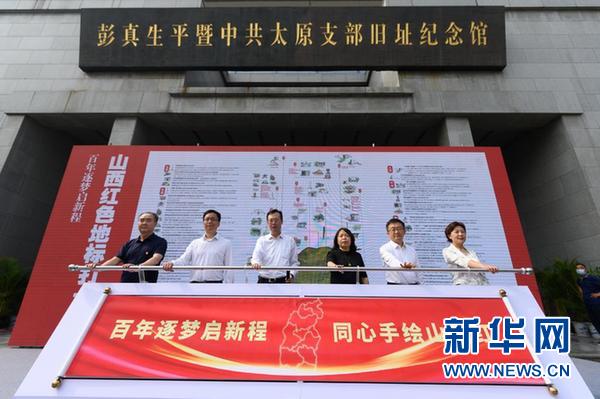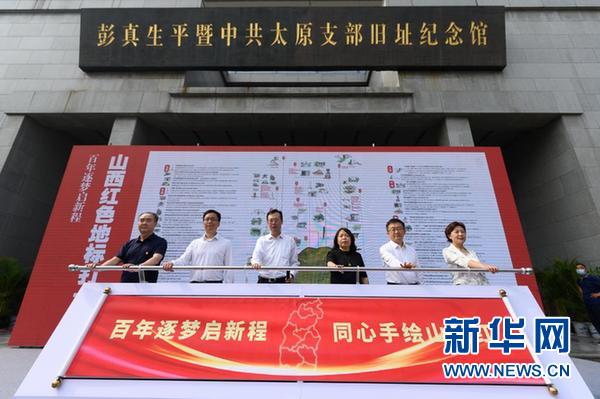《红旗谱》作为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经典,曾在创作发行之初获得颇多赞誉,其中,作家茅盾认为这部作品可以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小说作者梁斌,1914年生人,亲身参与“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他的作家身份和干部经历相辅相成,《红旗谱》所讲述的1920年代到1930年代抗日前的河北农村历史,都蕴含着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满腔深情,所以在简单的情节串联和人物设定的背后,却总有常读常新的现实价值和时代魅力。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红旗谱》的主题先行让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高调宣扬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随着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兴起以及新的批评方法的风靡,《红旗谱》获得更多新的阐释空间。其中,作家个体美学意蕴的发掘、历史真实与诗意虚构的互渗、民族形式(方言土语、地方风物与民间传统)如何弥合地方性与普遍性的革命叙事裂隙等等,这些不同面向的深入研究,成为《红旗谱》之于当代的意义显像,获得理论与现实层面的纵深感。然而,我们不难发现批评者很少在《红旗谱》中的爱情叙述上做文章。所以笔者以此为题,在谈论《红旗谱》中的关于爱的故事时,希冀挖掘关于对爱的深层理解。《红旗谱》写到了三代人,朱老巩、严老祥一辈在“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情节中作为序曲引出后续农民和地主豪绅的恩怨斗争。朱老忠、严志和作为第二代人成为农村阶级运动的核心力量,第三代是朱老忠和严志和的后代,大贵二贵、运涛江涛,他们后来居上,在共产党人贾湘农的启发下参与组织策划各项斗争运动。除去宏大的政治命题,回归到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里,每代人都用行动诠释出爱的意义。我想先从《红旗谱》中着墨最多的爱情——发生在运涛和春兰之间——说起。春兰是乡村姑娘,虽然黑瘦但心灵手巧,能拿得了绣花针也能扛得起锄头,性格外向热情,是个善良本分的好姑娘。运涛为人仗义、好读书,能接受新思想,对斗争恶霸势力、解除百姓忧危的共产主义运动心向往之。在书中有两处戏剧性地表现出两人感情深厚。其一,运涛从贾湘农处回村,路过春兰家便去找她。两人聊着宣传和组织的态度方法,春兰想打倒黑恶势力就可以和运涛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运涛则想着革命成功后的一片光景,想着想着,运涛以看手相之名攥起了春兰的手,这时觊觎春兰年轻貌美的冯老兰撺掇春兰大娘告诉春兰爸老驴头。老驴头一听春兰和运涛在厮混,本就不甚满意的他拿起小铁锹追着两人打,这时“运涛一愣怔,一时慌急,不知怎么好。又怕春兰受害,两手一舁,把春兰扛在肩上,撒腿就朝堤上跑。”对于情急之下的本能反应,运涛没有自己一个人跑掉,同时也想到了春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利己主义并没有在运涛身上出现,不仅体现了运涛对春兰感情至深,而且也为运涛作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埋下了有力的伏笔。其二,运涛听从贾湘农的话,去南方参加革命军,特意来和春兰告别。运涛怕自己一走回不来,“希望你另找一个体心的人儿”,春兰哭着想跳河自尽:“你革起命来,就有好光景了,还看得我穷人家闺女。”运涛瞪起眼睛说:“不管你等不等我,我要等着你!”运涛的誓言并没有来得及兑现,就被“清党”运动抓进了监狱。也因为这句话,春兰在运涛入狱后想让江涛带她去看运涛;也因为这句话,春兰果断拒绝了大贵家的说媒。她不怕村里的流言蜚语,她一直在等,从未动摇。女性对爱情的忠贞看似在微妙地重演“女性从夫”这一维护儒家社会和性别等级的千年旧戏,实质上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自我选择。这不是一种对道德规训的简单颠覆,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内在超越。春兰和运涛的爱情无疾而终,与其说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爱情显得微不足道,还不如说正是这种纯粹的对爱情的坚守成就了那些为国家勇往直前去奋斗的人。小说中,作为运涛和春兰的结构层面的接续者是江涛和严萍。而与春兰这一乡村姑娘不同的是,严萍是曾任教于保定二师的严知孝的女儿,身份地位自然要优于春兰。名人绅士的女儿被积极进取的革命青年感染,火红的赤色因爱情的热烈而高扬。运涛和江涛等第三代人的爱情,热烈中有崇高。第二代朱老忠的妻子是他在闯关东时娶来的,跟随着朱老忠离开家乡回到了锁井镇,极力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地陪伴着朱老忠走复仇之路;第一代严老祥自从朱老巩吐血而死之后便也被欺辱地离开了锁井镇,留着老奶奶一路守望和等待,直至运涛入狱老人弥留之际还在说:“老头子还不回来……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老奶奶在老头子走之后坚定地承担起整个家庭,以坚持等待的姿态给了整个家族以安定,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坚韧的革命。爱情作为人类传唱不歇的颂歌,展示着无尽浪漫、又吐露着些许哀怨。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在《人类的大地》这本书里写道:“生命教给我们,爱并非存在于相互的凝视,而是两个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方向。”也许,《红旗谱》中的爱所给我们关于“同一方向”的答案,便是以爱为基础又超乎爱之上的“革命斗争”吧!
关海潮 崔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