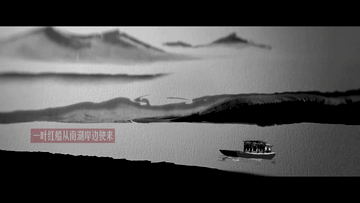五月的风轻轻的,风中总有一股淡淡的香。追着这香气儿,忽然就看见了一嘟噜一嘟噜的黄花花,小小的,密密匝匝地挤在一根根枝条上,笑吟吟、甜蜜蜜地随风摇摆着。怎么看,怎么都像咧着嘴、眯着眼的一群小姑娘。于是,那一棵棵长满了刺的沙枣树便更加地亲切了。它们站在乡野的路旁、水渠边、村里人家的房前及屋后,枝枝桠桠地顶着一身刺,像极了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庄户人。乡下的宅院前也曾有一棵沙枣树,长得极为高大,明显地高出荒野地里被风吹得歪向一边的那些沙枣树。那些沙枣树因为长年风吹雨淋,虬枝乱扎,像一个个无人管护、蓬头乱发的野夫,与村野的荒凉与贫瘠极为相应。而家门前的那棵沙枣树却长得潇洒俊宇,直溜溜的高出屋顶很多。当春天的泥泞褪去,嫩绿的麦子染绿了坡梁沟槽、扭动着柔软的腰肢时,一阵阵风里就飘出一股诱人的清香,一日日地,浓郁起来,直到五月的尽头。当秋天的大手拂过田野,收拢了一波又一波的绿,鼓噪了一个夏天的田野渐渐平静下来时,一串串金黄的沙枣便摇晃在风里,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儿。北方的五月,春意正浓,粉红的杏花儿刚刚缀满枝头,白嫩嫩的苹果花儿便飞上了枝头,紧接着是灿若云霞的榆叶梅,沙枣树却很迟钝,慢腾腾地抽着枝叶,直到那些娇艳的花儿美尽了风头,生出了一个个毛茸茸的小果果,田野四处,满地都飘着绿裙子的时候,那小小的、银灰色的花苞才张开小口,吹起一个个金黄的小喇叭,吐着香喷喷的气泡泡,在刚刚抹尽了香艳的空气中又荡起一波一波的香气。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母亲随手砍了野地里的几根沙枣树的枝子,把它们插在菜园子一角的那个豁口处,挡着村里胡奔乱蹿的牲畜。菜园子里的青菜绿了一茬又一茬,杏树、果树一年又一年地结满果实又落光。那围墙依然破破烂烂,但是,靠着突兀而起的荒草与左挡右挡的土块、石头,完好地保护着里面的每棵树、每棵菜甚至每棵草。母亲当年栽着的几根栅栏已经枯死在那里,独有一棵欣欣然地长成了一棵树,一年年地健壮起来,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树冠膨大而茂密,春天,高举着一顶花伞,金灿灿地闪着亮;秋天,拎着一串一串的沙枣,笑吟吟地站在家门口的正前方,欣欣然地望着我们。熟透的沙枣,红艳艳地馋着路人的眼,尤其经秋霜浸过之后,那味道真正叫甜。但是,它们高高地挂在半空,任何方来的贼也难以摘到。也许是受了菜园里的肥水滋养,那花儿开得特别艳,果儿结得特别大。而我们,也只能拽着它腋下的枝子,折几根花串儿插在瓶里,举着长长的杆子将那些诱人的果儿敲下来或由它们自然掉落。它既围护着家里的菜园子,又为夏天的我们遮着凉。坐在它斑斑驳驳的树荫里,看着层层叠叠的麦子、土豆偎依在白皑皑的雪山之下,在我们眼前翻涌着一片又一片绿波,任我们自由而又欢快的时光流逝在一个又一个暑假的午后。一季春去,一季秋来,我们渐渐远离了它,先是去外地求学,但每个寒暑假都能与它相聚,直到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安放在城市的一角,直到母亲身埋黄土,我们终于与它彻底别离,每天裹在拥挤的人群中寻着自己的目标。但它高大的身躯依然健硕,风吹不倒,雪也压不垮,沐着风雨,迎着阳光,守着咱们的老宅院。一晃眼,离开故乡已多年,它的香气一次次飘进我的梦里,一串串沙枣时常在我眼前晃呀晃……踏上回家的路,一草一木,一坡一洼里都是我的童年和少年。那条通向家门口的路已不再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老屋子却已衰蓑不堪,但那棵沙枣树总是站在家门前,远远地望着我,向我挥动着手臂。香气四溢,在每个春天,开满小花;在每个秋天,果实累累。可是,在那个秋天,它被断了根,彻底离开了我们,从此,永远永远成了我心底深处的一缕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