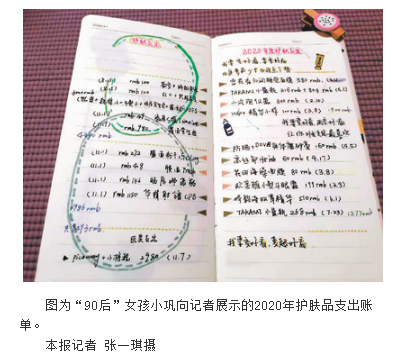很想拥有一把自己梦想中的紫砂壶,不为别的,只是想。在北京曾淘过一把自己喜欢的紫砂壶,喜欢它的手感、它的造型、它的大小、它原来的主人。曾在那个记不得名字的午后我和它的主人相谈甚欢,当然还有它的名字“西施”,因为我是极臭美的人。虽然年近半百的自己离西施越来越远,当时听说壶的名字叫“西施”自己竟然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喜欢紫砂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时自己贪恋生普。在婧那儿寻得并不多的两饼紫芽都是在北京用自己喜欢的精巧的西施紫砂壶给泡的,几乎每天下午一泡。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只用来泡生普紫芽的紫砂壶已经有些许淡淡生普的茶香,偶尔在不想做事情的时候我会爱恋地赏玩小小的西施壶,轻轻地摸索着,静静地观赏着,轻轻地闻着自己喜欢的香。准备离开北京时隔壁的姐姐前来相送,想着以后再也不会有之前性趣相投的日子,想着姐姐也是极爱茶的人,想着以后我们应该很少见面,我送给姐姐自己最爱的西施小壶。希望姐姐在忙碌之后、疲累之时,用我最爱的小壶泡一泡茶水慰劳自己,且一个人喝刚刚好。之后的日子再也没有遇上我喜欢的紫砂小壶,或许是曾经那把精巧的西施壶悲情地怨恨我爱时贪恋、转赠无念。后来的日子无论再怎么寻找,再也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小壶。与小小的西施壶擦肩而过的一段情缘曾让我一度怅然若失,或许我真是个薄情的人,失落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地忘记我的西施小壶,忘记了自己一度念念不忘的西施小壶上的那一袭茶香,于物而言,我终究会更薄情些。淡忘小壶的那些日子,自己也曾流连忘返于自己钟爱的茶馆,流连于家中的盖碗、紫砂壶、茶宠和茶香中,每每端起茶杯,心头飘过一丝失落,全然想不起失落的原因。在身体的零件七零八落地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日子,每日下午四点我会坐在萌的对面,或是自己静静地泡上或煮上一杯茶水。静静,实在不是因为我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因为第一次得了咽炎的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大夫说麻烦又不好去根的病。老公带着我去北京大医院看病,大夫说咽炎,应该是用嗓子过度,慢性病,很难去根,不好治。回到晋城的日子,老公说每天喝点老白茶试试。于是,每天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拿着自己存在茶馆的天青色的茶碗,开始了一个人静静地品功夫茶的生活。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不知不觉自己的咽炎奇迹般好了,自此我从生普的骨灰级粉丝变成了老白茶的粉丝。后来一直想试着养一把属于自己的老白茶的紫砂壶。再次有了养一把紫砂壶的念头,无意间又想起了曾经的西施小壶,精致小巧的只够一个人喝的小壶,好似我又拿捏它在我的股掌之间,似乎又再一次观赏它俏丽的脸庞,再一次抚摸它玲珑的身材,壶嘴渗透的点点茶汤如泪水梨花带雨般簌簌落下,倾诉着我们彼此久违的思念。那个擦肩而过融入我生命的小壶,如一缕烟随风而逝,但也如点点茶汤般水滴石穿住进我的思念里。老公不知从哪儿搞了两把紫砂壶,一个西施,一个石瓢。他问我:喜欢哪个?我没有回答,在审美上我俩从来不在一个频道,他喜欢厚重的、端庄的,我喜欢灵动的,纤细的。他先养了一把西施壶,不过这个做事较男人的同志还没养好壶,壶壶嘴就已经有些破损。心疼他拿回的手工还不错的紫砂壶,还有寻寻觅觅好久依然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对比之下我决定拿他的石瓢来养,用老白茶来养。拿着厚重的石瓢不禁笑了,如果之前我的西施是当下的小姐姐,那么这个石瓢绝对称得上小哥哥。拿着婧存放好多年的老白茶开始了养壶的时日,第一泡老白茶泡给闺蜜喝。因存放时间长,我那日泡出了如丝般的口感,还有浓浓甜甜的枣香。嗯,不错!就用这个家伙养我的石瓢了。说做就做,收拾起我能看到的婧的同款老白茶,幻想着一年或者两年之后又有一把小哥哥般自己钟爱的紫砂壶了。那个下午我使尽了十八般解数,用紫砂仍泡不出和闺蜜在一起如丝般的口感,以及甜得恰到好处的枣香,喝得还有点闷。于是第二天重新使用了盖碗,不错!还是婧的茶,还是泡出了和闺蜜在一起甜得恰当的茶汤,白净的盖碗就着金亮的茶汤,还是扑鼻的枣香,那是个沉醉其中的午后,于是那个午后自己放弃了用老白茶养石瓢的念想。细细想来,或许只用香高水薄的茶才适合紫砂壶,终究是自己想人定胜天了。无意间看到了老公放在电视柜里的铁观音,想着这是一款香高水薄的家伙,试着又用了石瓢,终于泡出了自己梦想中的乌龙茶的口感。茶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我用铁观音养石瓢终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老公回来说:老婆,你不是想用老白茶养石瓢,怎么又改用铁观音了?他不懂得女人是多变的,我更是。于茶我不懂,于壶我不懂,养壶我不专业。我只是喜欢无心间邂逅的喜欢,然后自己用心尽自己所能陪着她、他或者它们,在默默的陪伴中让他们喜欢让自己欢喜。用心养壶,用壶养心,用心养心,仅此而已。
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