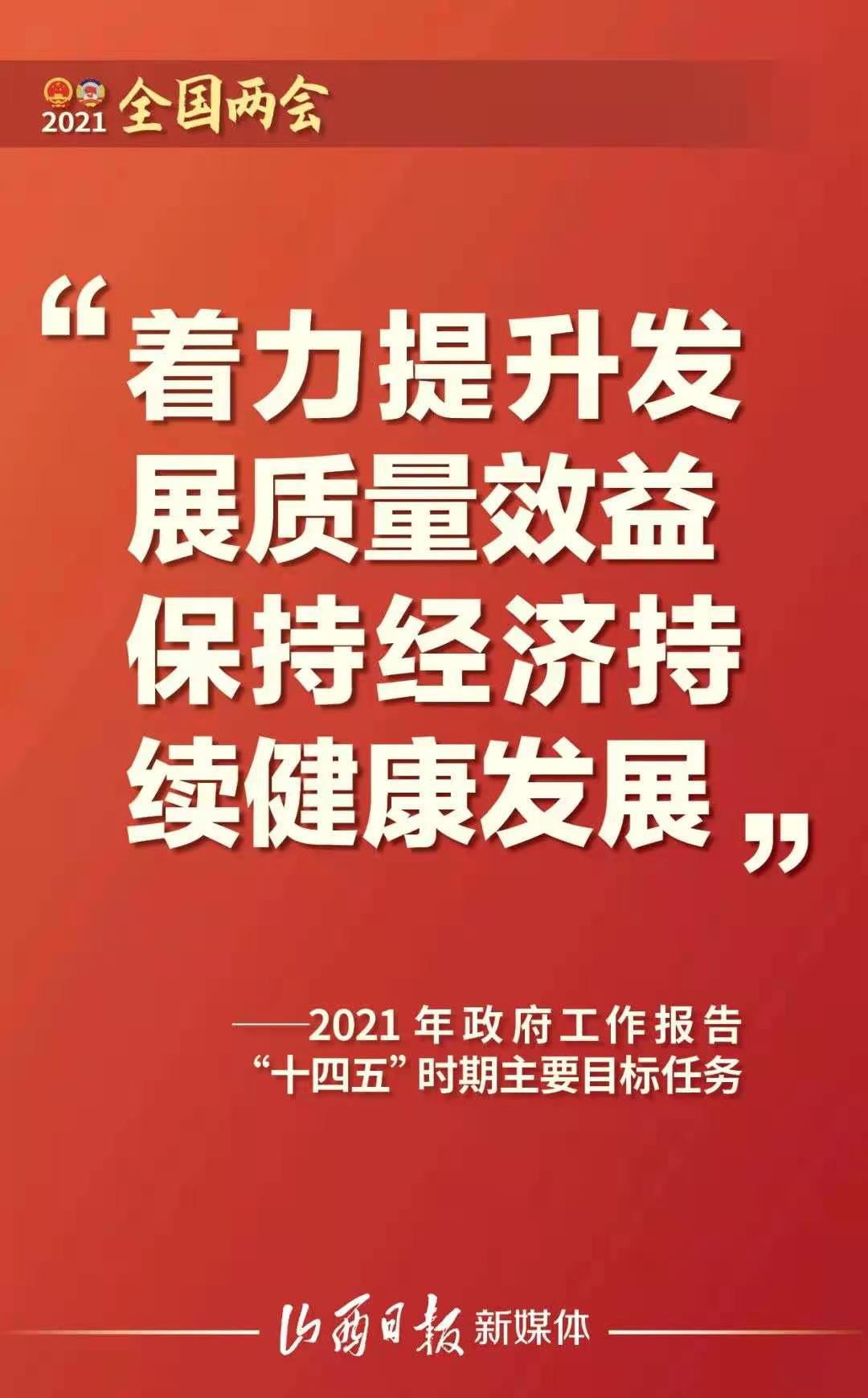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每次卖了粮食或者牲畜,甚至卖了鸡蛋时,母亲总要当着买主的面把钱点上几遍才放心。等忙完了一天,晚上,母亲还会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紧紧裹着的,鼓鼓的一卷,凑近煤油灯,一层层剥开,最后母亲才小心翼翼把一把零票票放在粗布床单上。这时候,我总能看到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她先把钱一张张整理好,再慢慢地数。数着,数着,母亲有时候还会往指头上吐下口水,再继续数。大约数到三遍,母亲确信不会错了,这才从枕头下面的席子底下,摸出一个鼓鼓的手帕,把手里的钱小心翼翼地和原来的钱裹在一起。我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母亲便从手帕里取出一些钱,她先数上好几遍。递给我的时候,还不忘叮嘱让我再数一遍,直到我报出的钱数和她的一样,她才点点头。临上学前,母亲又再三叮嘱我,到学校一定要先把学费交给老师,末了,她又给了我一张零钱,笑着说:“放学回来的时候,在校门口的代销点买几颗糖豆。”母亲没有读过书,但母亲会算账。那时候,一斤粮食两毛五,她居然能很快算出八百七十二斤三两粮食的钱数是多少。有时候我都有些惊讶,已经读初中的我,算这些东西都还要摆草稿,列算式,而母亲口算就能算出正确的答案。但只要我在的时候,母亲还是让我仔细地用笔算过,确认无误,她才笑着从小贩手里接过钱,又慢慢地数起来。我去外地上大学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母亲数钱。那段时间母亲每天除了干活之外,就是忙着走亲戚。三伏天里,母亲每天总是冒着酷暑,提着自家地里种的西瓜出去,等到天黑的时候才回来。从母亲那一声声轻叹里,我知道母亲有没借到钱。临开学的前两天,母亲让我和她一起牵着牛上集。我知道母亲想把那头老牛卖掉,但从母亲眼里流露出来的忧伤中,我知道母亲的不舍,毕竟那头老牛在我们家已经有十几年了。当母亲从牛贩子手里接过钱时,这一次她居然没有数,而是把钱直接递给我,她则用手摸了又摸老牛的头,强忍着泪水,背过身去。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而母亲也老了。母亲不肯去城里,她说她在乡下待惯了。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喂了一些鸡鸭,种了许多菜,从来也不卖。每次我们回家,她都会给我们装几大包鸡蛋鸭蛋和新鲜的蔬菜,让我们带走。那天,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笑着对我说:“光儿,正好趁你在家,把政府给我的养老金取出来。”当我把从镇上的邮政储蓄所里取出的一把毛爷爷递给母亲时,母亲乐呵呵接过去,仔细地数着,那神情,和当年是一样一样的。不同的是,她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明显地深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