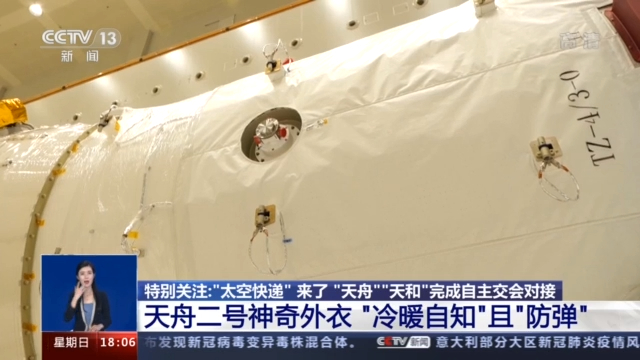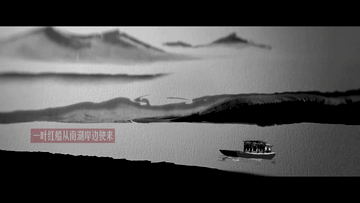我的老家在一个连名字都与粮食有关的小山村里,那儿的地不论块、不论亩,论的是“溜”。狭长的梯田沿山而上,每一溜只不过五到八米宽,老牛拖着犁耙走两个来回便能耕完。就这样的地,也都是一代一代的先人,用镢头一点一点开拓出来的。蚂蚁一般的乡亲们,就终年劳作在这样的田土之上。初冬时带着虔诚播下希望,来年夏天顶着烈日颗粒归仓。其间的几百天,则尽数被施肥、灌溉、锄草填满。地是山地,农人们必须挑着沉重的担子踩过小路、踏上田埂,才能把农家肥和清水输送进田中。黄土里有白色的石头,长得仿佛生姜。还有胶结在一起的土疙瘩,细碎且坚硬。这些都会令种子窒息,单凭镢头是应付不了的,需要用手捡出来丢掉或碾碎。爷爷和奶奶,衣服上是永远涤荡不尽的尘灰,指甲缝里是永远洗不净的泥垢。他们的手掌密布着角质,宛如干枯的树皮一般锋利。粗糙到足够把田土磨成最细的粉末,同时还精致到能从地垄中挑出散落的麦粒。到了收获的季节,爷爷走在头里,两头尖的担子上穿着半人高的麦捆;我和奶奶走在后边,柳筐里是金灿灿的零星麦穗。再经过连枷的拍砸、碌碡的辗轧、石磨的切削,这一年的收成才能安稳地落进肚腹之中。风吹麦浪是城里人眼中惬意的田园景致,麦子是矫情的诗人们笔下晦涩难懂的意象。但在我这样的农民的子孙看来,这些都脱离了麦子的本质。把新麦用水泡了,在研钵中小心地搓去外皮。熬米汤的时候加上一点,香甜的嚼劲儿给了农人最好的慰藉。用磨出的头道精粉做拉面,美美地“咥”上一碗,再端了面汤小口地嘬吸。这叫“原汤化原食”,那才是农人辛苦一年后的至高享受。奶奶告诉我,不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将来娶的媳妇儿脸上会长麻子,这故事让我从不敢浪费一星半点的粮食。爷爷去世之后,奶奶随我们搬到了城里。我生活的小城地处平川,周围也有着广阔的耕地。但里头不是连绵的大棚,就是密密匝匝的玉米,麦子倒是非常罕见的。儿子问我,咱们吃的米面从哪里来?很有幸,我的长辈都曾是种田的行家,我儿时也见识过乡亲们的辛苦,断不至于闹出“麦子长在树上”的笑话。但小孩儿并不满意于口头的答案,他想亲眼看看麦子和麦田。我们遍寻不见,只能告诉他有机会再说吧。机会自然是有的。那天,霄霄买回来一束装饰用的干花,里头就有两茎挺拔的麦子。儿子惊喜地问这是啥,我说这就是麦子啊。他又问咱们吃的面粉就是用它做成的么?我说是啊,这麦子长势很不错呢!它有着我们从未见过的粗壮麦秆,沉甸甸的穗子比成人的手指还长。儿子好奇地轻触着那尖利的芒刺,对我说:“很扎手呢!”我说是啊,一看就是上好的麦子。长辈们也围拢了过来,看着这束干花啧啧称奇。妈妈说真稀罕,还有用麦苗做装饰的?爸爸说搞不懂,也许是什么新美学风潮的实践吧?只有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还是麦苗啊,怎么就给割了呢?听到她的话,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才农历四月,距离麦熟还早。难道就为了做装饰,便把还在生长的麦苗割掉了?用手捏一捏那些籽粒,果然只是看起来饱满喜人,其实都是干瘪的壳子。尖锐的麦芒刺痛了手指,让我的心情忽地就沉了下去。爸妈的注意力也转到了麦穗上,一时间屋里所有的成年人都默然了。只有儿子还在急切地冲我喊着:“爸,你小心别把麦粒碰掉了!”我打开手机一搜索,很快就发现了相关的新闻。用尚未成熟麦子做装饰品,这竟然已经成了一些地方的新兴产业。看看那两株麦苗,它们的籽粒本来可以更加充实,穗子一定比现在还要沉重。可那样的话,经过干制以后,怕就不如现在看着挺拔了吧?我摇了摇头驱散了上一个想法——不对,麦子本就不应该是这种用途啊!奶奶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像她第一次看到平川上广阔的田野时一样。我记得那不过是一块撂荒的耕地,她却满怀深情地看了很久。她说:“多好的地啊”!又说:“怎么舍得荒掉呢?”撂荒的土地和早夭的麦苗,这是农人永远无心品鉴的风景。我看着还在欣赏花束的儿子,忽然很想给他认真地讲一讲,关于麦子的、不像故事的故事。
在水七方